一些精神分析領域的專家提出假設
他們通過對特朗普的觀察
認為他患有典型性的自戀型人格障礙
我們將要做的
是試圖沿著其人格分析的框架
盡量延展其有可能產生的國際政治觀念判斷
文 | 王一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
原載FT中文網,8600余字,閱讀約需13分鐘
美國大選結束后的第二天,《大西洋月刊》希望得到亨利·基辛格對特朗普是否適合做總統的看法。這名國務家的回復非常簡單,他說“我們得擱下這個問題了,他已經是經過民主選舉的總統了”。他又說,“沒有人能夠預見他的對外事務,所有國家都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學習(特朗普)。事實上,更為準確的說,是瘋狂的學習”。
以下是我的學習報告,謹以標題向那份塑造了半個世紀國際政治基本風貌的電報致敬,向一種遠為深刻的人格分析方法致敬,向過往歷史中無數次滲透給我們的古老教養致敬。
01
特朗普與自戀型人格
在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記述里,通過雅典人的演說,帝國的根本欲望被描繪為來自利得、恐懼和榮譽。兩千年后,霍布斯在《利維坦》第十三章“論人類幸福與苦難的自然狀況”里重復了這一古老訓誡。在他看來,人類進步的恒久動力也來自于此。而對于榮譽,他認為
“每一個人都希望共處的人對自己的估價和自己對自己的估價相同。每當他遇到輕視或估價過低的跡象時,自然就會敢于力圖盡自己的膽量加害于人,強使輕視者作更高的估價,并且以誅一儆百的方式從其他人方面得到同樣的結果。”
霍布斯筆下的榮譽,是很多偉大國務家畢生從事權勢競逐的核心理據,伯里克利會以之為名,向陣亡將士發布葬禮演說,拿破侖甘愿以永恒的戰爭為之獻祭。然而對榮譽的愛慕,往往是與利益的誘惑和對安全困境的恐懼同時存在的,如果后二者沒那么突出,如果貪戀名望成為個體合法性的全部來源,往往容易帶來個體欲望凌駕于政體利益之上的災難。
當代美國對于這樣的映像并不陌生。冷戰時期肯尼迪和赫魯曉夫在確保相互凌辱這件事上從來都是寸土不讓,從越南戰爭、克林頓的全球維和行動到小布什的伊拉克戰爭,無數次領導人的個體意志先行于戰爭的應有裂痕。立于山顛之城,擁有一定程度的個體英雄主義甚至自戀,是相當正常的事情。在肯尼迪眼里,除了麥喬治·邦迪,所有人看起來都像是傻瓜;約翰遜總是格外注意保管個人物品,哪怕只是一張廢紙屑,在他離任后,約翰遜總統圖書館不費吹灰之力順利建成;而克林頓和奧巴馬則永遠與人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整個任期幾乎沒有與任何國家的政要建立親密的朋友關系。
然而現在大家都知道了,不會有任何一位總統能夠呈現出特朗普這樣的個人風貌。除了競選時的帽子和離任時的圖書館,不會有人在任何物體表面頻繁刻下自己金色的名字;不會有人在競選時告訴選民,我們需要一位寫過一本名為《做交易的藝術》的書的人來擔任總統;即便在離任后,也不會有人敢于說自己就是成功的,而特朗普在競選之前,就已經將這一點視為上帝的意志。
的確,如果按照霍布斯的釋義,利益和恐懼很難成為特朗普前行的動能。對于一名個人資產超過歷史上所有總統之和的成功人士而言,
“金錢很難再帶給我刺激,除非它能繼續給我加分”。
他所指的加分是人生意義上的,或許可以暫且簡單而粗略地理解為——更高一級的個體追求。這種追求與霍布斯描繪的榮譽很像,正如他的著作所提到的,
“當人們看錯你時,要繼續跟著這些家伙(證明自己)。當他們看到你跟上來時,這種感覺很好,我甚至會覺得更爽”。
這種追求驅動著特朗普的整個人生,從一名優秀的學生到出色的華爾街精英、再到1987年接受采訪時所首次暗示的,“總統是我喜歡的獵物”。
追求榮譽自然是一種偉大的抱負,然而特朗普似乎在這條路上走過了。去年宣布競選時,“清晰政治”網站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提到,
“從臨床上看,自戀狂一般自命不凡、極度自滿、嗜好吹牛、對自己認為不重要的人肆意侮辱、不給別人說話機會、認為自己擁有特權、一旦覺得沒有享受到這個特權就大發雷霆。綜合特朗普在競選初期的表現, 幾乎和這些特征一一對號入座”。
而后,一些精神分析領域的專家提出假設,他們通過對特朗普的觀察,認為他患有典型性的自戀型人格障礙,在責任心、外傾性、宜人性、穩定性和開放性五個方面的行為特征都處于極端位置。礙于醫學界的“金水法則”(如果沒有經過專業醫務人員的檢查,禁止對公眾人物的患病情況發表評論),這一說法只能停留在未經驗證的經驗判斷上。在被確立為共和黨候選人后,這種猜測越來越多,特朗普的很多做法讓人們想起了杰克遜總統曾經給美國政治帶來的無序,人們也開始擔憂核密碼掌握在一個情緒極其不穩定的人的手中是否會給國家帶來災難。而后不久,2.5萬人在change.org請愿網上聯名要求對這位總統候選人進行心理健康測試。
這些擔憂沒有確鑿的證據,但即便是在字面意義上,人們也傾向于認為自戀型人格障礙就是特朗普所呈現出來的那個樣子。在《做生意的藝術》書中,通篇充滿了“我”、“特朗普”、“我們”這樣的字眼,這絕對不是一本簡單的成功學著作,而是一本建立在第一人稱視角下具有極強的壓迫性說教的書籍。《自戀和精神失常的領袖》一書的作者瓦克寧通過對特朗普600小時講話視頻的研究發現,在單位時間內,他的第一人稱單詞頻率遠遠高于其它歷任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眼里從來沒有其他人,即便就站在眼前,他也可以完全無視。在勝選后發表演說時,特朗普感謝了十余名他覺得為競選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每點到一個人名,緊站在他身旁的副總統彭斯就會附和著鼓掌,然而一直未輪到他自己。直至整個演說結束,特朗普回身準備下臺之時看到了彭斯,匆匆說了句,“也感謝彭斯”,而后轉身離去。
如果你覺得這樣的行為實在粗魯,那么當初介紹彭斯擔任競選伙伴的提名演講簡直堪稱災難。那場演講的內容大致是這樣展開的——
“彭斯……我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看法是對的……彭斯……希拉里是個奸詐的騙子……彭斯……我在脫歐問題上的看法是對的……彭斯……希拉里滿嘴謊言……我們會讓煤炭業重新發展起來……基督徒喜歡我……彭斯……我講話是有統計依據的……彭斯長得不錯……我在華盛頓的酒店真的越來越棒……彭斯”。
用《紐約時報》的評論來說,
“特朗普跑題大放厥詞的時間是他介紹彭斯的時間的兩倍都不止。甚至連彭斯恭維他的時候,他都拒絕留在臺上,用贊賞的眼光專注地看著對方。那場面就像是看一個新郎在新娘上場時對婚禮喪失了興趣。”
這種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在特朗普的身體內是通透的,不區分對象的。《大西洋月刊》在另一篇有關特朗普性格分析的文章里提到了1999年特朗普在父親葬禮上的致辭,他在開頭提到,“這是父親人生最為艱辛的一天”,而后便立即轉向自己,“然而他最為偉大的成就就是養育了一個頗負名望的億萬富翁兒子”。特朗普家族的傳記作家布萊爾記得,第一人稱的單詞隨后干脆驅散了所有的第三人稱,父親不再被提及。當所有人都在追憶的時候,特朗普一個人對于父親的偉大遺產(他自己)夸夸其談。
盡管看起來滑稽,但這些畢竟還都是自戀型人格障礙呈現正面狀態的時候。作為一種醫學意義上的疾病,自然也會擁有典型性的負面問題,其標志性特征就是對于外部環境過于敏感,自尊心極其脆弱,自我保護意識極強。
特朗普沒有足夠的朋友,這一點在整個競選過程中都十分明顯。特別是在最后的沖刺階段,當克林頓夫婦在最后幾天內與奧巴馬夫婦、拜登夫婦和各路明星歡聚之時,特朗普身邊沒有布什家族,沒有羅姆尼、麥凱恩、保羅·瑞恩,只有家人。特朗普的內心是在意的,他抵抗孤獨的辦法是孔乙己式的激烈反抗,他無數次地在自己的演講中跑題式的列舉好友名單,一個一個點出名字。在競選的最后一天,他提到有200名軍官支持他,還提到新英格蘭愛國者隊的比爾·比利切克和湯姆·布雷迪在投票后專門給他寫了贊揚信。遺憾的是,民主黨陣營隨后采訪了布雷迪,后者迷惑地表示,還沒有去投票,狠狠挫傷了特朗普的自尊心。
“偷稅門”也是如此,類似的抨擊在歷屆總統競選中常常會出現,特朗普一向樂于公開炫耀自己的公司和資產,按理說應該不會懼于公開任何信息。一種比較主流的分析認為,由于在競選初期曾經宣揚過自己的身價為100億,而很多金融分析機構早就指出其身價不過30億左右,特朗普擔心公開公司報稅信息后丟掉面子。單從性格分析的角度來看,這的確可能成為特朗普的隱憂與痛苦,特朗普也是會為了掩蓋這一點而付出一定的輿論代價的。
自戀心理的終極合法性在于自身的完美受到認可,而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終極夢魘就在于這種亟需的認可沒有得到應有的愛撫。特朗普很敏感于身上不夠完美的地方,他的管家就曾記得他由于身材較胖幾乎從未在家中的池塘邊穿過泳褲;他的首任妻子伊萬娜曾經由于在滑雪時嗖的從身邊越過,惹得特朗普直接大怒,脫掉滑雪板并步行下山休息。一個更廣為流傳的故事是,
1980年《名利場》的編輯卡特曾經嘲笑過特朗普是一個“短手指的俗人”,25年后,他仍然會在郵箱中收到特朗普寄來的照片——手握著金色的Sharpie筆,以顯示他擁有正常尺寸的手指。三分之一個世紀后,馬克·魯比奧在競選又撿起了這個話題嘲笑特朗普,后者再次勃然大怒,并且以更其下流的詞匯予以了回應。
通過競選總統,特朗普如愿為人們所關注,他的很多觀點、語匯、手勢、習慣為人們所熟知,草根階層把他視為強權者、反抗者、救世主,精英階層甚至把他視為法西斯式的災難,所有這些標簽充斥了人們的觀感和認知,在極大滿足、反復撩撥特朗普虛榮心的同時,也集體構筑了各式各樣不夠準確乃至虛假的特朗普鏡像。其實,自戀無法等同于強硬、獨立、反抗或者革命。自戀的終極價值只有一個,就是自戀本身,其它所有的價值意象不過是圍繞著為它服務的,不過是因由這些意象可以更有利于實現自我傾慕。反過來,一旦有所需求,沒有任何標簽是不可拋棄的,這或許也將解釋特朗普將如何逾越競選承諾和執政實際之間的巨大鴻溝,關鍵時刻下,現實政治仍然是第一位的。
然而自戀型人格這一基本經驗判斷是沒錯的,這一特朗普人之為人的終極合法性來源是不會被丟棄的。當我們沿著這次競選閱讀他的傳記,觀看他在早年接受采訪的很多片斷,我們驚奇地發現,特朗普的很多言論不是競選對抗的應激性產物,也絕非幕僚團隊制定的政治正確邏輯,而是他人生實實在在的積淀,是他實實在在的人性風貌。這種風貌促成了他的成功,也因由這份成功所反向塑造,并最終推動他從Trump Tower的電梯走下來宣布競選。對于特朗普而言,競選能夠帶來一個更廣的舞臺、更多的觀眾、更大的榮譽,甚或遠遠高于榮譽的個人滿足感、宣泄話語霸權的沉醉感、揮灑個體意志的權力感。而這些,是其行為的全部根源。
02
特朗普的國際政治觀念
戰爭結束后,喬治·凱南寫下那份著名的八千字長電報——“蘇聯行為的根源”,主要目的是通過對蘇聯民族性格的深刻揭示,為杜魯門政府的國家利益界定和對蘇戰略提供路向選擇。在特朗普的人格風貌已經如此具有辨識性,甚至成為其行動的主要驅動邏輯的情況下,同樣的研究方法是可以被再次嘗試的。
在《大西洋月刊》的采訪中,基辛格認為,特朗普除了表示將親自搞定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兩筆交易(特朗普所言的交易是指與這兩國的對外關系處理)以外,幾乎沒有提及有關國際秩序、國家利益的任何界定。而冷戰以來,美國的國家利益界定已經習慣于按照喬治·凱南等幾代戰略學家們創建的輕重緩急次序,進行普遍主義-特殊主義、全球性-區域性的劃分,從“新面貌”、“靈活反應”、“緩和”到“世界警察”,每屆政府對于國際政治的情勢判斷多有不同,但整體的邏輯和范式是一致的。希拉里在競選中所提出的對外戰略是傳統主義的,某種程度上比奧巴馬還要傳統,帶有明顯的冷戰意象。這嚴重脫離了當代選民的欲求,被特朗普粗糙地打著孤立主義的旗號奪走了勝利。然而現在當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特朗普的這份孤立主義,我們發現這樣一個單詞甚至根本無法描述國際政治各個維度的復雜意象。我們將要做的,是試圖沿著其人格分析的框架,盡量延展其有可能產生的國際政治觀念判斷。這樣的方法或許沒有充足的理據,但是可以提供一種經驗分析的視角,而在此刻,這種基礎性的冒險是絕對必要的。
1
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
特朗普生長于一個威權式的家庭,父親弗雷德·特朗普是在皇后區與布魯克林區靠自力更生發家致富的地產商。特朗普在幼年成長中一直被冠以“有錢仔”的名號,盡管他做了很多努力,仍然很難融入身邊階級屬性不同的伙伴。特朗普為了證明自己,只能刻苦的學習,并保持一直成為最優秀的學生,而其代價就是愈發的孤立并慣于自我欣賞。在幫父親做監工的日子里,他們常常一起巡查自己的社區,他漸漸發現每次父親敲完門后都會悄悄站在門楣以外的部分,父親告訴他這是為了防止里面的人由于不信任直接開槍。這段經歷對于特朗普的成長十分重要,讓他發現了這個世界不可信任的最初原罪。在他看來,今天的華爾街就是那扇虛掩的罪惡之門,槍口就在門后,他就站在門楣之外。
按照馬斯諾的需求理論,絕對安全永遠居于個體和國家利益的頂端。自戀型人格的內心是足夠敏感的,外部環境的變化將帶來巨大的情感暗涌,而避免這一憂慮的唯一辦法就是追逐絕對安全。刻苦學習可以獲得絕對安全,把所有人攔在門外也是一種絕對安全。特朗普的那些要在美墨邊界修建長城,抵制穆斯林入境的主張聽起來荒謬,更像是為了在人數眾多的選舉政治中凸顯而出,然而這是他從小與少數族裔絕緣的生存環境塑造的,也是他尋求絕對安全的一種避險方式。在特朗普看來,只有這種方式才能真正驅散美國本土四處雜生的社會問題,確保美國本土的絕對安全。
另外一個層面的絕對主義反映在其對于國家道德的判斷上。瓦克寧教授通過對特朗普愿意給人起外號的特征分析,認為特朗普擁有主動尋求敵人的天然嗜好。只有通過確立攻擊對象,并且將其徹底擊倒才能凸顯出自身的合法性,“與人斗,其樂無窮”已經內化為特朗普重要的性格特質。在他看來,特朗普的世界是黑白映像的二元對立——“如果你不是100%順服于我,你將110%的成為我的敵人”。這個世界是有好人和壞人之分的,來自新澤西州的克里斯蒂就是好人,希拉里就是壞人。對于好人他會在每一場演講中不惜花費時間專門提到他的名字,并且加上“他是一個好人,一個非常好的人”這樣的評語。而對于壞人,他將附以畢生的憎恨,不惜用最惡毒的言語展開持續的攻擊。記者科潘斯因為曾在一篇稿件中認為特朗普深愛的馬阿拉歌別墅有點兒過時,特朗普就憤怒到每天都要發好幾條推文予以報復,說他是“不誠實的懶蟲”和“真正的垃圾,沒有信譽可言”。這樣的攻擊持續了整整兩年,甚至讓科潘斯覺得自己已經躋身特朗普最為深惡痛絕的前10萬人之列。
經典現實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利益而非國家道德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如果對于個體道德的愛憎分明轉移到對于國家道德的判斷上來,則極為容易出現國家道德僭越國家利益的現象,回到威爾遜主義的老路上。從目前的觀察來看,特朗普篤信絕對主義而非相對主義的解決方案,就他已經明確表態的對于恐怖主義和極端伊斯蘭的憎恨來看,是包含著強烈的善惡判斷的。我們有理由期待,在特朗普的任期會重新出現小布什政府提出的“邪惡軸心”這樣的名詞。
2
現實主義與強人政治
特朗普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這一點毋需置疑。制度和規范在他眼中不值一文。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時殷弘教授所言,“特朗普從未對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規則體現出哪怕最為起碼的尊重”。從現實主義的權力觀來看,特朗普對權力的理解更像是自戀型人格障礙界定的一種被稱為“上帝光環”(God-Like)的心理,本質上是一種站在更高位置擁有操控能力的個體滿足感。特朗普的父親從小就希望他在市場中成為一名具有攻擊性的“殺手”和“國王”,他選擇的方法是把特朗普送進軍校,而那是一個在特朗普的回憶中“非常強勢、非常粗魯的地方,到處都是能把你打出屎的警官”,這段經歷徹徹底底教會了特朗普什么叫做強權。擁有權力,可以不被欺辱;擁有權力,可以“把ISIS打出屎來”;擁有權力,就可以給那些美國的敵人用上最為嚴酷的刑罰,讓他們知道,特朗普就是上帝。
基于同樣的邏輯,特朗普傾慕于強人政治,陶醉于強人之間分享如何把玩權力、操控政治的快感。所有人都能感到,特朗普與普京之間存在著一種莫可名狀的默契和欣賞,這種強人之間的或明或暗的互動必將在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成為重要的國際政治變量,影響其對外政策的制定。反而觀之,由于其一貫的歧視女性的立場,默克爾、特蕾莎·梅現在應該深陷苦惱,她們將發現很難再去全然仰賴大洋彼岸的自由精神,身處特朗普和普京兩個“直男癌”之間讓她們深感不適,這一點從默克爾的祝賀電報里就能夠發現。同時,更為明顯的是,特朗普將必然反感于制度安排下的各種束縛,他篤信赤裸裸的權勢力量,在《做交易的藝術》一書中,特朗普指出他成功的核心要義在于“要把目標定的非常高,然后不斷地壓迫、壓迫、再壓迫,確保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在他看來,權勢可以改變一切,包括制度和規則,他要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重新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而很多與他合作過的商人都記得,特朗普酷愛起訴別人。
在《大西洋月刊》看來,由于特朗普在兩院和聯邦法院的反對力量將極其警惕,特朗普政府將很有可能重走尼克松政府的路線,對外事務強硬、務實,內部事務對選民蒙蔽、狡猾,充斥著馬基雅維利式的功利。這一點有來自“政治真相”網站的數據作為支撐,盡管特朗普一直攻擊希拉里是個騙子,然而通過對競選階段特朗普演講信息的甄別,該網站發現,其中
“有2%的內容是真實的,7%的內容絕大部分真實,15%的內容僅有一半真實,15%的內容絕大部分虛構,42%的內容是虛構的,18%的內容簡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3
孤立主義與商業精神
特朗普從未有過任何領域的執政經驗,他本質上是一名商人,他幾乎天性地會關注自身的資產負債表和資本回報率。在特朗普看來,新保守主義以來復雜不堪的全球干涉格局已經使美國不堪重負,整個國家的負債表在全世界范圍內傷痕累累,一名商人下意識的反應或許就應該是放棄那些不應有的負債項目,為國家的全球義務瘦身,這與孤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謀而合。
如果再把資本回報率的概念映射到國際政治的現實中,其所指代的應該是如何帶來更好的霸權收益。在特朗普看來,對于那些已經產生依賴的“順風車”國家,享受帝國的佑蔽是必須交出保護費的。這一體系是否應該繼續維護,深深的取決于體系的歷史成本、維護費用和收益。特朗普把簽訂一份好的合同當成是十分重要的商業原則,認為NAFTA和TPP都是非常糟糕的協定,因此不惜違背契約精神,也一定要重來。
然而徹徹底底的孤立主義或許并非特朗普的本意,他只是想通過孤立的威脅去懲罰那些在過去依附于美國治下的和平卻不支付費用的國家,一旦建立了平等的買賣關系,美國還是會愿意繼續提供公共物品,這還是一樁好的交易。而對特朗普而言,他的興趣終究會回到對外事務上的。
強烈的外交動能是特朗普政府的必然表現。這是真正的他所覬覦的舞臺,一個可以在各國政要面前施展個人威望、宣泄話語霸權的舞臺,這應該是最能治愈特朗普的自戀型人格障礙的地方。特朗普是那樣的充滿無窮無盡的身體能量和展示自己的強烈欲望,他曾經說過自己晚上睡覺的時候也在清醒地想事情,人們經常驚訝地發現他的整個下半夜一直在發出推文。國內來自政黨和利益集團的阻力往往束縛過多,惟有在國際舞臺上,才擁有相對寬松的自由度,才可以肆意把玩外交賦予領導人的獨有權力,以高壓的權勢逼迫那些他認定的敵人向美國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致敬。
4
可信性與合法性
最后,讓我們再來看一看美國的國家榮譽。如果說特朗普上臺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認為奧巴馬使美國衰落下去了,而他要挽回這份國家榮譽,“使美國再次強大起來”。特朗普無疑是愛國的,這與其深愛自己的邏輯毫無二致。可以想象,在其任期內,美國例外主義會進一步擴張,他會視國家的面子為特朗普自己的面子,并竭盡所能予以維護。
人們傾向于從特朗普反復多變的性格擔心他治下的美國是否還會擁有冷戰以來賴以維系其權勢的重要財富——可信性。這一點毋庸置疑,正如上文所提及的,特朗普黑白分明,他劃定的己方陣營就是己方陣營。鐵桿兄弟克里斯蒂在競選階段出了很多亂子,特朗普從來都沒有把他丟棄;競選經理萊萬多夫斯基被媒體哄吵毆打女記者,特朗普第一時間出來為其站臺。我們幾乎一定看到這樣的時候,他在普京面前喋喋不休,“我在拉美有很多盟友,在亞洲有很多盟友,中國最近與我的關系不錯”。特朗普是會愿意維護美國的可信性的,因為信任的對象是特朗普,他不會容忍任何盟友國家對自己流露出失望的態度。
最后,讓人們最為擔心的是,特朗普對于政績合法性的瘋狂追逐。不難想象,特朗普如此重視美國的國家形象,會像每天必須親自梳頭一樣親自打理美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很多面子工程,幾乎一定會饒有興致地每天觀察美國國家股票的漲跌。一旦國際社會看低美國,特朗普必將動用權勢和外交能量竭力為美國的國際地位護盤。
這中間最大的危險在于,自戀型人格有一個死循環的邏輯,就是要無限制地證明自己是對的。正如一位醫生所指出的,
“患者對于事實本身根本不甚在乎,如果有人提出質疑,會充滿能量的做出更大的動作向你證明”。
這一點在特朗普的身上十分明顯,他在整個競選階段接連換了兩位競選經理,幾乎每一位離開的人都是因為無法說服他不要大放厥詞,而特朗普總是會再下一次演講中把話說到更糟,拼命證明自己不會因之遭到懲罰。現在看來特朗普贏了,他一定為自己的極端表現開心不已,并認定這種游戲邏輯是正確的。而如果他把這份開心和自信帶入到新的國際政治的舞臺上,必將引發無數場博弈論中常常提到的“針尖對麥芒”、“膽小鬼游戲”式的循環困境,給國際社會帶來極大的緊張和徹底的失序。
通過對小布什伊拉克戰爭的考察,很多分析人士指出,為自己父親的伊拉克政策進行辯護的心理,是小布什發動戰爭的主要因素。在《大西洋月刊》看來,特朗普與小布什一樣,一直在用畢生的氣力尋找名垂青史的功績,一旦有機會,是一定會做些什么事情來實現這一夢想的,即便甘冒巨大的風險也不為過。因為這將建立個人意義上巨大的“情感回報”(Emotional Payoff),極大地撫慰其自戀的心理,使其深深滿足于其中,并在歷史中永遠留下自己的合法性。
面對特朗普,中國的選擇?待續······敬請關注
轉載請注明來自夕逆IT,本文標題:《上海代表處賬務處理與報稅指南:流程詳解及關鍵點提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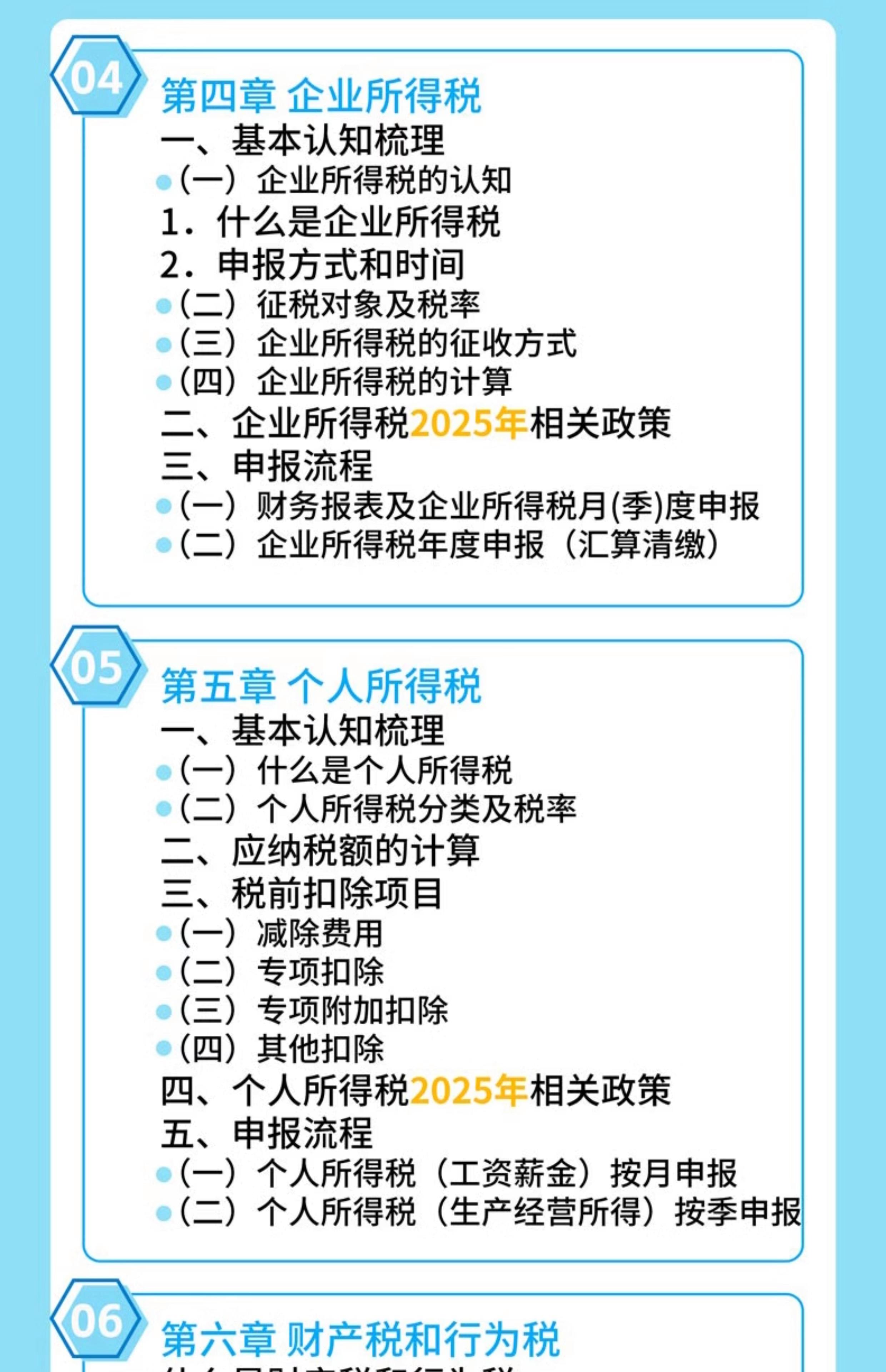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00000000001號
京公網安備11000000000001號 京ICP備11000001號
京ICP備11000001號
還沒有評論,來說兩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