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特輯
“聽說過沒見過兩萬五千里,有的說沒的做怎知不容易,埋著頭向前走尋找我自己,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在一所大學的體育館里聽到崔健演唱這首《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時,我被其中內蘊的激情深深震撼。歌聲中迸發出來的力量感,能讓一團青春的熱血燃燒起來。聽這歌時也許我不見得會想到不怕犧牲、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等這些代表了“長征精神”的語詞,但我能體會到人在絕境中求生的強大意志。用今天的話說,歌里溢出的是滿格的正能量。
崔健
上世紀30年代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個壯舉。兩萬五千里的救亡圖存之旅,爬雪山過草地啃樹皮吃野菜,時刻面臨死亡威脅,過程中并無什么浪漫可言。那不是一場驢友們的草原雪山深度游,不是野外生存拓展訓練或真人CS野戰游戲,既不“布爾喬亞”,也不“波希米亞”。在充滿敵意的殘酷環境里,生命隨時可能被剝奪,而你卻不能像打游戲或者做惡夢時那樣,摁下“重啟”鍵,聽到“叫醒”鈴。
長征是一曲蕩氣回腸的英雄之歌。寫過《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的斯諾、寫過《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的索爾茲伯里,都把長征描繪成偉大的“史詩”,而那個名叫布熱津斯基的前美國官員甚至贊嘆道:“對嶄露頭角的新中國來講,長征的意義絕不止是一部無可匹敵的英雄主義史詩,它的意義要深刻得多。”
布熱津斯基
史詩是令人敬畏的,我們需要心存這么一份對歷史、對英雄的敬畏感。有人把重走長征路視為“朝圣”,有人把長征看成凝聚理想信念的神圣“圖騰”,有人把它看成引領民族復興的精神“路標”。這樣的理解都很好,它們不是那種把形式意味看得比內容還要大的政治抒情。長征本身已足夠偉大,浮華的高調反而會損害人們對它的景仰。我們只需要尊重事實,發揚長征所稟有的史詩氣質,就可以對抗今天甚囂塵上的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虛無主義有很多種表現,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刻意消解歷史敘事的真實性,曲解歷史事實本身所蘊含的意義,模糊正義與邪惡、崇高與卑怯、進步與落后的邊界,要么以一種表面上的客觀性擱置對歷史的價值判斷,要么索性以重構和質疑的名義行價值顛覆之實:或虛化焦點,以枝節遮蔽整體;或去中心化,以邊緣替代主流;或突破底線,用畫虎類犬、點金成鐵的方式,用“惡搞”“戲謔”的態度,肆意褻瀆和丑化英雄。 虛無主義者其實并非真的“虛無”,而是有著很強的執念。他們冀望在被解構的“歷史”的瓦礫堆中扒拉出滿足自身需要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就像病毒侵蝕一個民族健全的機體,在歷史虛無主義的語境里,像“理想”“信念”這樣美好的語詞都會顯得極其可笑。
長征是革命先輩留給今天人們的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因為擁有這樣的遺產,我們就不會輕易被虛無主義俘獲。英雄先烈是值得銘記也應該被銘記的,否則就像魯迅當年充滿悲涼地感嘆的那樣,“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英雄主義史詩的原址上將升騰出新的精神。我們回頭張望,是為了確認方向和位置是否適當。有人說,沒有故鄉的人身后一無所有。當年長征路上的每個人都在尋找自己信仰的故鄉,新長征路上的我們,也一樣。
韓少功
作家韓少功曾寫道:“ 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從陌生中尋找熟悉,讓遙遠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無限往事。人可以重新選擇居地,但沒法重新選擇生命之源……”是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時代的孩子,如果切斷了與那一段烽火歲月相聯結的精神臍帶,我們就不過是一群迷惘而棲惶的孤兒。在今天這么一個所謂的“后現代游樂場”里,我們尤其需要從那些跋涉險山惡水的前輩身上汲取勇氣、韌性和力量,要知道那些衣衫襤褸的紅軍戰士,比今天很多搔首弄姿、無病呻吟的嬉皮士們“酷”上一百倍。他們意志堅定。他們樸素無私。他們有大無畏。他們沒有茍且。他們吞咽苦難卻締造幸福。他們戰斗的人生充滿審美的張力。如此看來,把長征解讀成一種超級勵志的人生哲學,也未嘗不可。
轉載請注明來自夕逆IT,本文標題:《歌詞聽說過沒見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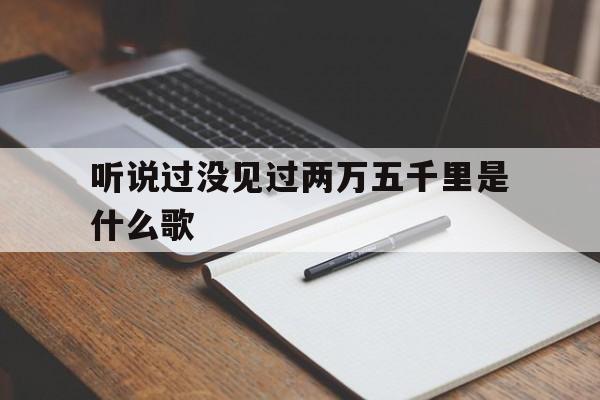
 京公網安備11000000000001號
京公網安備11000000000001號 京ICP備11000001號
京ICP備11000001號
還沒有評論,來說兩句吧...